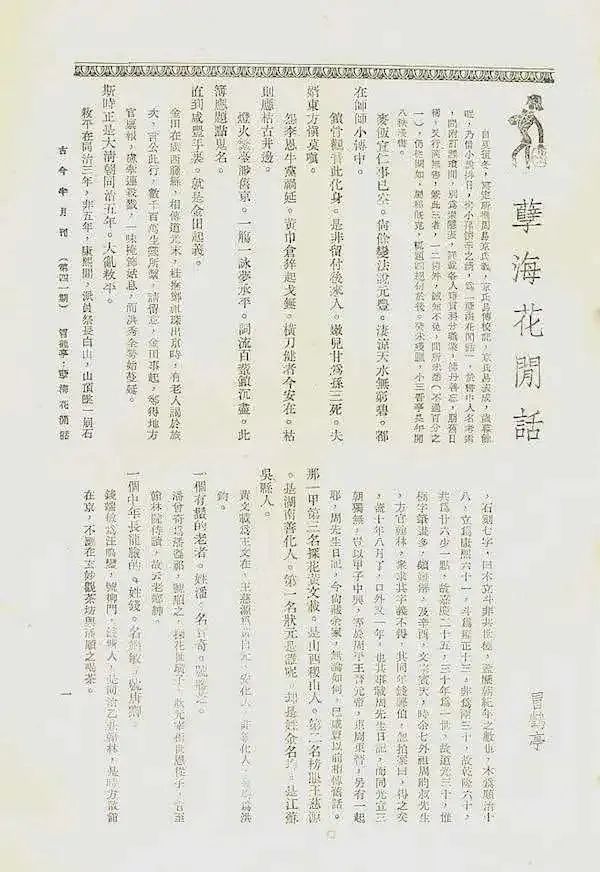静安区延安中路的模范村,曾住着一位赫赫有名的文坛大佬,现在已很少有人提起,那就是冒鹤亭先生。
文|管继平

▲模范村管继平摄
中国历史上冒姓的文化名人是极少的。说起来明末四公子之一的冒辟疆,无疑是最为著名的了。冒辟疆是江苏如皋人,如皋有个水绘园,即谓当年冒辟疆与董小宛的栖隐之地,如今已成了南通首屈一指的园林名胜了。除了冒辟疆,著名人物大概就数民国的诗人学者冒鹤亭了。
冒鹤亭先生经史子集,无所不通,特别是在诗词上的成就,于近代史上颇有举足轻重之地位。曾著有《小三吾亭诗》《小三吾亭词》《后山诗注补笺》《四声钩沉》《宋曲章句》《疚斋词论》等多种著述。
冒氏为江苏如皋的大族,书香传世,源远流长。而且,如皋冒氏的源流来自于蒙古,祖上是元太祖成吉思汗的嫡裔,元亡后其子孙流落江淮,一支就在苏北的如皋落户,遂姓为冒氏。鹤亭先生也是江苏如皋人,所以明末的冒辟疆与民国的冒鹤亭,本为一族,都为蒙古人的后裔。假如冒辟疆留下的画像尚不作凭的话,我们只需从冒鹤亭的照片来看,其面相饱满,颌下有须,比之当今歌手腾格尔,也颇有五六分的神似,可见冒氏为蒙古人之后裔,绝非虚言。

▲冒鹤亭先生
虽原籍如皋,但冒鹤亭却是生在广州,和许多“京生”“沪生”一样,父亲为他取名“广生”,鹤亭乃其表字。说来还是非常巧合,冒鹤亭生于一八七三年阴历三月十五日,他居然与冒辟疆是同月同日生,只不过相隔二百六十二年罢了,故时人惊奇地称他为“冒襄复生”。而且,幼年的冒鹤亭“早慧有声”,与当年的冒辟疆一样,都有“神童”之誉。
尽管鹤亭六岁失怙,其后读书皆随其外祖父周星诒及外祖伯周星誉传授。这外祖的周家兄弟都是山阴读书界的名人,周星诒精于校雠目录与史学,是有名的藏书家;而周星誉能词善文,时任两广盐运使。冒鹤亭幼年在外祖身边读书,获益无穷,七八岁就能写诗属对,深得外祖伯的赏识。那段时期,两位外祖的著述稿本,都成了他翻阅诵读的资料,尤其是外祖父的《南齐书校勘记》《三国志校勘记》以及《书钞堂藏书日记》等,实乃冒鹤亭少时博览群书、研习经史的最早启蒙,影响则贯穿了一生。待十七岁时,他回家乡如皋参加科考,其时考秀才要经过县、府、院三试,冒鹤亭却以三场头名的“小三元”佳绩,中了秀才。至二十一岁,他又考中了举人。本来他还是有机会再中进士的,光绪二十九年(一九〇三年)他应经济特科试,被主考列为一等,可是复试在策论中他引用了法国哲人卢梭的《民约论》,恰被对此有所偏见的首席读卷大臣张之洞审阅,阅后批道:“论称引卢梭,奈何?”张还调侃说“姓卢的人家有好人么?梁山卢俊义是强盗,洛阳卢莫愁是女娼。”其实张之洞欲擢拔自己的门生,冒鹤亭遂被摒弃,以致错失了一次良机。

▲法源寺诗社雅集,左三为冒鹤亭先生
虽科考止步于举人,但冒鹤亭在经学、史学、诸子以及诗词文章等领域的学术成就还是颇有影响,名气也不小。入民国后,冒鹤亭在袁克定的邀请下,曾先后做了温州、镇江、淮安等地海关监督、外交交涉员。虽身为关长,但他却无意于仕进。他年轻时曾有“白头不作功名想”的诗句,尽管诗是写给桐城的前辈文人萧敬孚先生的,不过也应该带有自己的同感。故冒鹤亭每到一处,总是注重发掘一些地方上的文献名胜,或搜集整理前贤诗文刻版印书,或募资修葺古迹。所以,陈三立曾有诗赠冒鹤亭云:“抱关碌碌竟何求,不狎鱼龙狎海鸥。乞食情怀天所鉴,扬芬事业梦相谋”,说的即是此意。鹤亭先生在温州的任上,做了很多“不务正业”的文化工作,如从《元诗选》《明诗综》及方志等书搜集丛残,编成《柔克斋诗辑》《永嘉诗人祠堂丛刻》等;此外还刊刻《永嘉高僧碑传集》等,难怪著名书画家也是温州人的马公愚曾对人说:“在温州当官的前后不知多少,早为人们遗忘,记得的只有冒监督。”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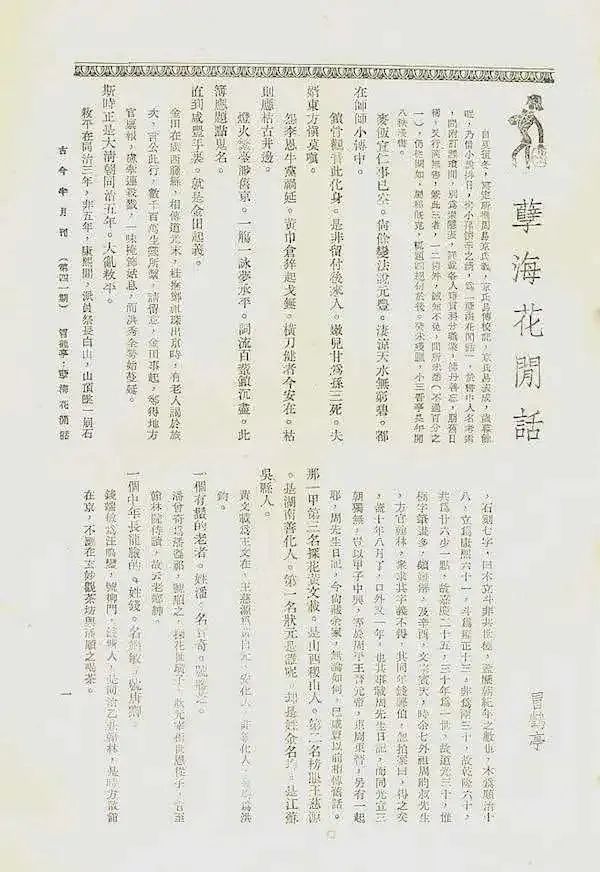
▲冒鹤亭先生所著《孽海花闲话》
上海图书馆所藏的一通手札,系冒鹤亭致广东番禺叶恭绰的信。叶恭绰字裕甫,号遐庵,在民国时曾任交通总长等大官,但他出身世代书香门第,对诗词书画、金石鉴藏等无所不精。冒鹤亭与叶恭绰两家有三世之交谊,冒鹤亭的青少年时期都在广州,他的词学老师拜的就是叶恭绰的祖父、著名词学家叶衍兰先生。叶衍兰先生与冒鹤亭的祖父也是故交,其时叶先生任越华书院的山长,在几位弟子中独对青年冒鹤亭格外器重。后来冒鹤亭宦游离粤,他曾在冒鹤亭的词集序中说自鹤亭去后,“岭以南,无有如鹤亭之可与言词者”。在越华书院时,冒鹤亭二十来岁,风采动人,才华纵横。而此时的叶恭绰年仅十二岁,也在书院玩耍。春秋佳日,后堂丝竹,那时的两人就已经结下了交情。尽管按世交算起来他俩也属同辈,但因冒鹤亭年长八岁,故叶恭绰在书札函件上总是放低自己一辈,尊称冒先生为“鹤丈”。当然,被尊谓“鹤丈”的冒鹤亭本人,则不可能倚老卖老,他与叶恭绰仍是言必称“仁兄”。
遐庵仁兄阁下:弟以一年来手战极怕写字,大抵性愈急则愈战,字愈小则亦愈战,此后恐将成废人矣。李宷言遗著,弟准助刻赀五十元。惟另募则殊不易,不若将弟名义附入尊募三人之一,似两省事。疏香集早收到,谢谢。委选花影吹笙两词当如命。惟手边无书盼各寄一本,当于十日内报命,并将旧撰词话之语加入。词话一书已由唐圭璋觅得送来。惟当日本非完书,拟补足成之。将来当将应补之词之人向尊处商借,大约亦不过十数家耳。乔石林象已由榆生处转奉否?匆复并颂
日祺!
弟广生顿首一月廿九
此信应是冒鹤亭晚年所书,因鹤老自述写字已有手颤的毛病,而且如“性愈急”“字愈小”的话,则症状愈烈。不过,就此函的墨迹来看,虽字亦偏小或稍有颤笔,但书法的矩度还基本存在,风致不减,更无所说的那种颤抖而不成字的弊病。就我们常见的几幅鹤老书法来看,其擅长的还是小字为主,尽管他不像叶恭绰那样而有书名,但他一些诗稿尺牍皆端庄清润,疏朗蕴藉,落笔干净,少有俗尘。
我书架上有一册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上海古籍出版的《冒鹤亭词曲论文集》,其中就有一页鹤亭先生的词稿手迹,虽也是先生晚年八十六岁所书,而书风恰与此手札相仿佛,秀劲澹逸,精神不老。
鹤老一生喜整理汇刻散佚诗文,为保留和传播先贤的文化遗产尽力,此习至老不变。这通书札与叶恭绰所谈的也是,先是主动愿意助资五十元,加入叶恭绰的“三人募资小组”,以帮助整理刻印“李采言遗著”出版。
李采言,直隶冀州人,又名李青峰,采岩。一九二七年李大钊就义时,他曾经冒着极大的风险,在李大钊家人痛苦、艰难无助的关键时刻挺身而出,携带李大钊的两个才十多岁的女儿,到下斜街长椿寺认领李大钊遗体,为先烈重新装殓入棺。后又是他将李大钊的书籍杂物领回保存,还将烈士的遗孀遗孤接回自己家暂住,再安排车辆将她们送往东车站出京,回乐亭县老家避难。当时人们皆以为李采言是李大钊家乡的一位“远房亲戚”,其实不然,李采言曾就读于天津北洋法政学校,他和李大钊是该校预科英文甲班的同窗,关系非常密切。
鹤老此函一通两页,选用的是淡朱色“考试院考选委员会用笺”,原件今藏于上海图书馆。通过图片,我们可清晰地看到右上角有叶恭绰收信后的批注:“鹤亭来书奉阅,乞告李世兄,范九先生。绰上。”我想这里的“李世兄”,也许就是李采言之后人。而“范九先生”,应该是南通的古籍名家,也是与叶恭绰素有交往的费范九先生,因为费先生精于古籍整理出版,曾主持影印过宋刻“碛砂版大藏经”,叶恭绰将此信告之,也许“李采言遗著”的刻印之事即交予他承办。
叶恭绰自少年与冒鹤亭相识交往始,他们保持了长达一生的友谊。翻看那部三十余万字的《冒鹤亭先生年谱》,叶恭绰是出现名字最多者之一,或书信往还、诗词唱和,或陪同鹤老游南京,或在北京、上海等地,随处皆可见叶恭绰之“身影”。
冒鹤亭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起,即住上海延安中路的模范村,其时与一批活跃于海上的书画名家如王福厂、贺天健、吴湖帆、周炼霞、张善孖张大千昆仲、谢稚柳夫妇、钱瘦铁、唐云等,都有交往。其中吴湖帆、周炼霞还常以自己的诗词请鹤老指点。一次叶恭绰陪鹤老赴嵩山路的吴湖帆寓中,赏鉴所藏的历代书画精品,后应吴湖帆之请,由叶恭绰代鹤老在其所藏的元王蒙《青卞隐居图》下端的裱旁题上了“丙子五月,冒广生、叶恭绰同观”十二个字。此卷也属传世经典,裱绢上已有罗振玉、郑孝胥、陈宝琛、张学良等名家题词,如今此幅名画连同这些名家题辞,都成了上海博物馆的珍藏了。


▲延安中路模范村,冒鹤亭先生曾住22号
冒鹤亭先生的晚年基本都住在上海模范村寓处,直至终老。其间曾于一九五七年到北京的幼子、剧作家冒舒諲的家中小住了大半年,分别受到毛泽东、周恩来的邀请,礼遇晤谈。其实,冒鹤亭先生一九四九年自南京返回上海定居后,时任上海市市长的陈毅就已经亲自到模范村二十二号拜访了鹤老。临别后,考虑到鹤老暂无收入,先送上一笔钱。一个月后,即派人送上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特约顾问的聘书,月薪三百二十元。还专门关照:“毋庸办事,陈仲弘表示其优礼耆儒意耳。”
鹤老甚为感激,专门题写了扇面,并请吴湖帆作画,托江庸转呈陈毅市长,以表谢意。鹤老于一九五九年以八十七岁的高龄寿终而寝。
作者介绍
管继平
1962年生于上海。笔名推仔、易安阁等,上海报业集团高级编辑,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、上海作家协会理事、上海市文联委员、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、上海书法家协会常务理事、上海楹联学会副会长、顾振乐艺术馆馆长。

选稿:许文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