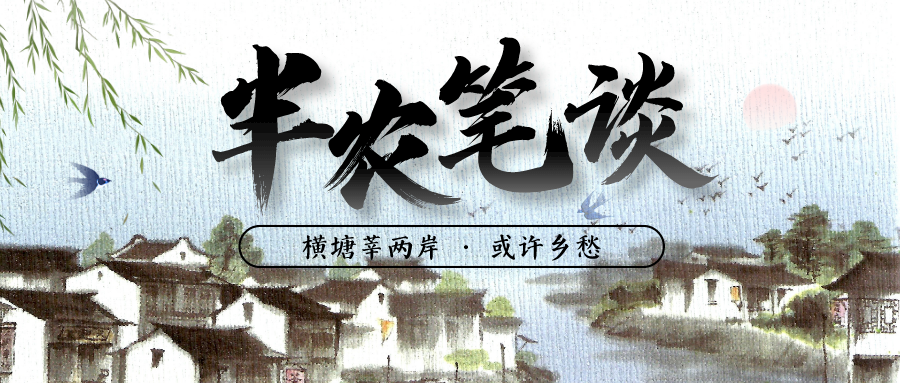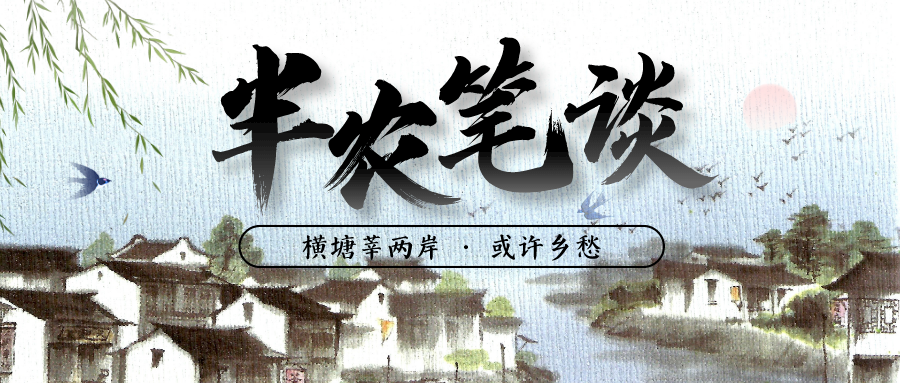
近日来,根据金宇澄长篇小说《繁花》改编、王家卫执导的同名电视剧热播,这部上海原创、上海制作、上海出品的电视剧,几乎全上海演员班底用沪语来演绎故事、塑造角色,让上海土壤里生长出来的上海话,响彻荧屏内外。
本期“半农笔谈”,让我们跟着沪上知名方言、方志研究者,闵行本土作家褚半农老师一起来了解小说《繁花》里的上海方言词语——
金宇澄获“茅盾文学奖”的小说《繁花》(上海文艺出版社2013年3月版。下同)使用了大量的沪方言,数量之多,在我阅读过的当代沪(吴)语长篇小说中第一次遇到。我大约莫统计过数量,书中的名词、动词、形容词、熟语总数要超过1100个(条),还不包括副词等虚词,和其他如俗语、谚语等。它们在小说中为展现地域特色,勾连故事情节,塑造人物形象发挥了独特作用,也为方言在当今使用现状留下了记录痕迹。这么多的方言词语中,有老里老早流传下来的老派词语,也有这几十年中产生的新派词语,它们在小说有用得准确的,自然也有可商榷之处,总的情况是同当今社会上使用上海方言的态势基本相一致,可作上海方言研究的一个标本,值得重视。
说说《繁花》中的“只”字
量词“只”在平常生活中常用,尤其是上海方言中,普通话中少用或不可用的地方,都会用“只”字。这是量词“只”的基本用法,金宇澄的长篇小说《繁花》中也有,如“一只掼奶油圆蛋糕”“三只单人沙发”等(玖章·贰,第117页)。
《繁花》中另有种量词“只”字,是同“人”搭配起来使用的,显得较特殊,还大量出现,如“四只夜游神”“几只瘪三”,听起来是不是怪怪的?这种怪怪的“只”字,在小说一开始的引子中就出现了第一例例句。说的是梅瑞跟沪生谈恋爱,一次去看电影,两人在电影院卡座里坐下后“刚刚一抱”,有人拍了一下梅瑞肩胛,这个突然降临的动作可把两人吓了一跳。梅瑞抬头一看,是一个“黑宝塔样子”的女人,自称同梅瑞是“姊妹淘”,还要约他俩电影散后一起吃夜饭。梅瑞拉了沪生马上就走,到外面后忿忿不平地说:“这只黑女人,学农时期房东女儿”。(第4页)
量词被人们视为汉语实词中的“小词”,它的作用除了有如《现代汉语词典》所说的“表示人、事物或动作单位”基本功能外,还有描绘形态、表达感情的特殊作用。当然,这要靠打破常规来实现,如移用其他类型的量词,即打破量词和中心词的搭配规则,把原来同甲搭配的量词,移用于乙,以适应表达的需要。方言中“只”较多地用于动物,如“一只猪猡”“两只狗”,现在将它移用于人身上,就产生了特殊的表达效果。设身处地地想一想,如果彼时彼境,梅瑞对坏她好事的那个女人用的量词是“个”字,当然也可以,但不足以表达她心中“忿忿不平”的愤怒心情。在这场合,用“只”字最恰当,不可改动。
这类“只”字,《繁花》中共使用了47个,分散在17个章节的41个句子中。表示对象是女人的有24次共25个,表示对象是男人的有17次共22个。按照《上海市区方言志》(许宝华、汤珍珠主编:《上海市区方言志》,上海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,)的说法,“只”用于称人时带贬义,指人品不好者(第404页),这类“只”字《繁花》中也有。有的只是泛泛而用,感情色彩较少,如“陶陶叹息说,这只女人,就等于独裁专制,我要民主自由,我怕的。”(四章·一,第54页)从陶陶嘴巴出来的这个“只”字,语气比较平缓,也完全可用“个”来替代。
但书中更多的“只”字是为了表达说话者的情感和情绪,就是要让对方“不好听”。这类“只”字后面带的基本都属詈词,计有26种说法,其中22种(约占85%),就是骂你,是痛骂,欲置对方于死地,如骂女人的用婊子、赖三、女流氓等,骂男人的用赤佬、小赤佬、老棺材等,这些名词本身就是詈词,前置“只”字后,则强化了骂詈功能。这种表达说话者极度憎恨、愤怒的“只”很多,如“二十四章·二”中,“小阿嫂立起来说,我怕啥,两只东京来的婊子,两只上海赖三,打呀,我好人家出身,我怕啥。”(第325页)事情发生在饭店聚餐时,女人之间因相互看不顺眼,加上平时裂隙,言语发生冲突。小阿嫂用“只”字,就要让话语带愤恨色彩,还依照怀恨程度,在量词后用上不同内容的指称,这里是婊子、赖(lá)三(女流氓)连用,可见双方之间积怨甚深,当然她的解气、回击的目的也达到了。
“只”作指称人的量词何时出现?在我的阅读范围里,清末民初上海滩有名的两部社会小说中已出现这种带“只”字的例句了,如:
“这一家堂子里出进的都是些上海寓公宦家公子,对于别人都是什么刘二大人、孙三大人、杨四老爷、汪五老爷乱叫,独独对于石牌楼只秃头叫一声老爷,表示这位是他们自己的老爷之意。”(包天笑著:《上海春秋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5月版第94页)
老七对空骥斜瞅一眼道:“你只马总是这般瞎三话四,你不要我陪……那么对不起,明朝会!”说着飘然而去。”(网蛛生著:《人海潮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5月版第695页)
前一个例句中,石某从前做过道台,堂子里的湘老七嫁给了他。湘老七的娘又开了家妓院,石是女婿,底下人自然称他为“老爷”。但他又是奔六十的人,加上是秃顶,现在加了个“只”字,明显表明尊重中有疏远,尽管用的是作者口吻。第二例中,老七是妓女,空骥姓马,也是称呼她的相好,这样称呼符合两人的亲昵关系。
“只”在上海方言中,还有个常见用法是省略前置的数词或代词,这多发生在单数时,如“一只戆大”“迪只瘪三”,就可说成“只戆大”“只瘪三”,表达效果一样。上引《上海春秋》和《人海潮》小说中也是这样使用的。而在松江府原住民方言口语中,这种用法更是常见。《繁花》中有30个“只”用于单数,似也可照此办理,省略代词“这”,但书中未见有这种用法的例句。
这种“只”字的生命力极为顽强,时至今日,依然流传有序。不仅口语中常常听到,连媒体上也常能看到带“只”字的例句,限于篇幅,只举一例,还是上海隔壁苏州的事例:
外婆的想法很简单:嫁给我爸,我妈就能调到小镇工作,好歹离上海近些。我妈指着外婆说,要不是你,我怎么会认识“这只男人”。(路明《上海来的外婆》,2019年2月12日《文汇报·笔会》)
这是母亲说父亲,她的婚姻基本是由其母亲作主的,近乎包办,有个曲折过程,“每次我妈对我爸有所不满时,她会觉得,这一切的问题都是我外婆引起的。”其中“这只男人”表达方法反映了她的复杂心情,“只”字上反映出的不满,一箭双雕,不仅是对自己丈夫,也有对母亲。
选稿:许文杰